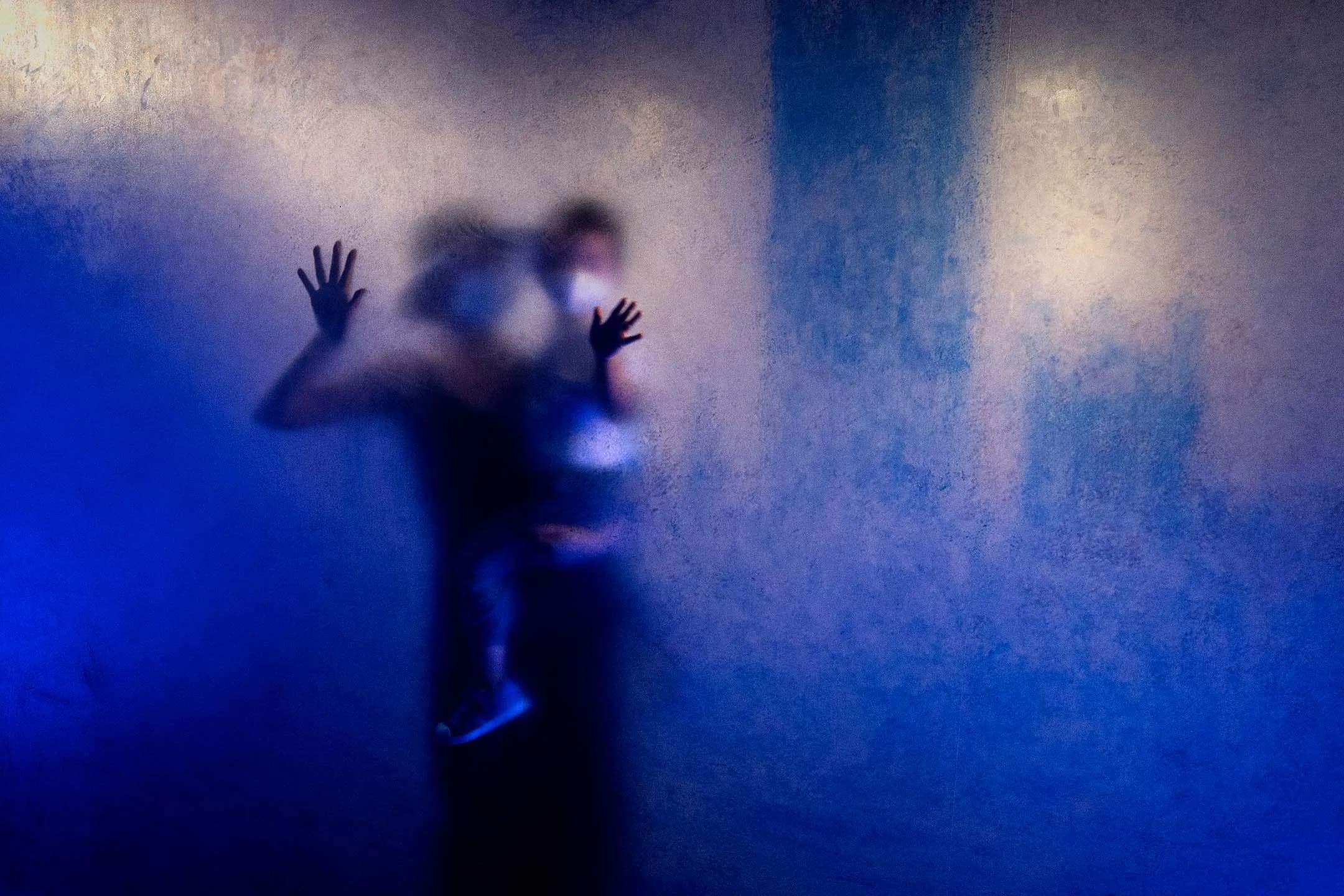
(李大猫,中国文化、互联网研究者)
在日渐缺少活力,挤不出有实际意义的热词的中文互联网上,2023 年夏天 “厌童” 一词绵延月余的热度确实罕见。当然,争论的形式毫不新鲜:从丽江不欢迎儿童的咖啡馆、高铁儿童哭闹被歧视、再到韩国无儿童区普及…… 擅长总结现象、诊断 “病症” 的媒体将零星的 “舆情事件” 串联起来,再用一贯的 “当代年轻人图鉴”“这届年轻人……”“那些 xxx 的年轻人现在都怎么样了”“北上广的年轻人,现在正在……” 等句式,总结出可供传播的热词。2020 年代,中国年轻人总是遭到反复诊断,毕竟 “这届年轻人” 贫乏的生活几乎是当下简中语言唯一被允许丰富的地方。
不出意外,厌童被诊断出的 “病因” 仍旧是 “独生子女经历 / 边界意识强 / 工作压力大 / 生活空间小”。这些原因也被用来解释恐婚恐育、断亲(不和亲戚往来)、宅家、躺平、反内卷、算命、搬家去鹤岗等一系列现象。毕竟经济紧缩的当下社会弥漫着焦虑和悲观的氛围,被视为累赘的又何止是儿童。不过,除了帮工作和婚育双重压力下的年轻人哭惨,厌童的话题值得进一步发掘:是否想要生育子女更多取决于对较短时期内生存状况的权衡和预期;但如果真的出现了对广泛的儿童群体的厌弃,则意味着整套社会观念的系统变化。
当然,我们难以精确统计人们对儿童态度的变化,但根据《澎湃新闻》最近发起的调查🔗,已育和未育人群中表示可以忍受儿童吵闹的均不到一半。进一步说,“能不能忍受孩子” 会成为一个话题,本身就暗示了变化 —— 在主流舆论渲染儿童是祖国的花朵、纯洁的安琪儿的时代,这个问题根本不会被毫无顾忌地公开讨论。
社会对儿童态度的变化之快往往超乎人们的感知。外 / 祖父母抚养儿童的隔代养育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少数情况,但 2021 年的统计显示🔗,城市各年龄段儿童中受到隔代养育的近 80%,农村则在 90% 以上。两代人教育和抚养理念的巨大差距往往在小家庭中制造激烈的冲突。成人对待儿童态度和方式的变化,既取决于社会发展状况和生活水平,也取决于围绕年龄的知识和文化的生成。
其实,现如今的 “儿童” 概念本身就是一种只有三四百年历史的文化;在中国甚至只有一个多世纪,和反殖民、社会启蒙、现代化追求、中产阶级发展都大有关系。在整个二十世纪,儿童曾扮演多种重要角色,如今时移势易,与其说是年轻人越来越厌恶儿童,不如说儿童这个社会角色正在失去其社会意义。
“发现” 儿童,需要经济基础
世事艰难的时候,儿童的性命尚难保全,“童年” 的概念就更难成立。
21 世纪所讨论的厌童是相对于现代 “重视儿童、喜爱儿童 “的社会仪轨而言的,但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成人对儿童都不甚在意。

在漫长的古代,人类的平均寿命时常只有三四十岁,婴儿夭折率更是极高,今天可以预防和治疗的百日咳、白喉、麻疹、水痘、天花等传染病都是致命的。即便晚近如明清、优越如皇室也是如此。比如顺治皇帝生育了 14 个子女,只有 4 子 1 女活到 7 岁以上;康熙之所以能 8 岁即位,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得过天花而获得了免疫力,有更大希望活到成年。古人应对婴幼儿高死亡率的方式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多生,但避免在一个孩子身上投入过多物质,尤其是感情。历史学家在《儿童的世纪》一书中提到,中世纪的欧洲人对待孩子就像一些现代人对待宠物:宠溺(mignotage)逗弄但并不在意。很多婴儿夜间在全家人睡着的拥挤床铺上被疲惫的父母压死。人们甚至会这样安慰已经育有多个子女的产妇:“在这些小淘气给你制造许多麻烦之前,他们就可能死了一半,甚至全部死了”。
除了自然夭亡,在生活条件恶劣、又没有重视儿童文化的时代,弃婴和杀婴非常普遍。古希腊和罗马,子女是父母的财产,弃婴是管理家庭规模的常见手段,有一系列诸如 Ektithêmi(暴露,类似英语 expose)等词语来委婉地表示这种行为,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神谱》和悲喜剧中充满了这样的记载。在日本,江户时期经济泡沫破灭、生活水平陡降导致了杀婴的大流行。人们为免良心揹负杀人的负担,发明了杀婴还神的说法:七岁之前的孩子是神的孩子,如果没有养活或杀死,就是把孩子还给了神明。中国出土的秦朝《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即有禁止杀婴的规定,历代关于杀婴的刑法愈发严峻,这种行为仍屡禁不止,在宋、清两朝尤其严重。
宋朝杀婴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苛捐杂税,时人描述为 “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苏轼在书信中写道, “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 一个 “辄” 字道出了杀婴之普遍。南宋国土面积缩小、军费增加,平民的赋税压力更加沉重。因为国家地少人多,按人头收取的 “身丁银” 成为盘剥百姓的主要方式。因此,尽管南宋朝廷大力鼓励生育,但无人响应,反而是杀婴愈演愈烈。
清初因为生产力发展、税制改革等原因,人口激增超出了土地承受能力,导致广泛饥馑,“薅子” “洗儿”(都是杀婴的委婉说法)成为风气。《二十四孝图》中 “郭巨埋儿” 的故事在今天被视为愚孝、残酷、反自然的代表,但在 “二十四孝” 流行的清代,人们有不同的逻辑。康熙年间的《福惠全书》写道:“(百姓杀子)盖因贫不能自赡,, 而又乳哺以妨力作,, 襁褓以费营求,, 故与其为一以累二,, 毋宁存老而弃小”—— 老人有养育之恩和浓厚亲情;而婴儿尚未和成人建立牢固的情感纽带,不仅难以存活,还会拖累孕产妇、减少家庭劳动力。
抛开孝道,“存老弃小” 甚至是某种理性的选择。清代还有一种特殊景观:婴儿塔。其外形是佛塔,供人抛弃婴儿,任其自生自灭。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战乱贫困之下婴儿塔仍有人使用。左联五烈士之一,22 岁遇害的诗人殷夫的代表作《孩儿塔》就是关于这一习俗的。
世事艰难的时候,儿童的性命尚难保全,“童年” 的概念就更难成立。欧洲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中涉及的婴儿形象(比如达芬奇笔下的圣婴)大多是被画成等比例缩小的成人体态,乍看有些怪异。这种绘画表现的不是当时的儿童,而是当时人们关于儿童的观念 —— 小一号的成人。颇为伤感的是,七八岁之前的孩子不被当成完整的人,七八岁之后有自理能力的孩子就直接被当成大人,承担家庭重担。平民家庭的孩子不是和父母一起做农活,就是在城里当学徒、助手、跑堂或仆役,换取免费的食宿和一技之长,女孩还可能关在家里学习家务女红。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就要正式组建新的家庭,中外大体相似。
富裕家庭的孩子可以接受教育,免于直接参加劳动。但教育场所中往往不同年龄学生杂处,不仅有和成人世界一样严格的礼节、仪态要求,课程的内容也是直接围绕成人世界中的职业准备。中国古代的私塾首要是面向科举;今天焦虑的家长送学龄前的幼儿提前学习中小学课程、训练特长、外语、编程…… 名义上是启发智力,培养兴趣,实际上也是类似的逻辑 —— 成人世界的生存压力太大,家长希望孩子尽早准备,提升自己未来作为成年人力资源的价值。

欣赏儿童就是相信进步
在中国现代化话语中,儿童是属于未来的进步力量;是民族乃至人类的希望。保护儿童,就是保护民族和人类的未来。
那么,纯洁、天真、充满希望、需要呵护的 “儿童” 概念何以诞生?这个渐进的过程得益于现代化过程中生活水准的改善、中产家庭生活方式的形成和人文主义的思想改革。
在欧洲,婴幼儿存活率逐渐提高,鼓励成人在他们身上倾注感情。同时,形成中的民族国家逐渐削弱封建贵族、庄园主的势力、打散庞大的家族、行会等社会组织,把人们作为个体重新组织为国家的公民和劳动力。在这个背景下,能够自由流动的原子化个人组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这种新型的核心家庭不再仅仅是物质生产的联盟,而逐渐继承了其他社会组织的情感功能,家人之间更加亲密。同时,中产阶级 “男主外、女主内” 的生活模式确立,妇女被排除出职业生活,成为了全职的儿童养育者。
17-18 世纪,儿童专门的服装、用具、读本和关于育儿技巧、儿童生理心理特点的书籍开始大量出现。中产阶级家长不再让孩子去别人家做工,而是让他们在家庭教师和学校的帮助下接受启蒙教育。儿童专门教育的出现,要得益于人文主义,尤其是启蒙运动让人自身成为了哲学和科学探究的主要对象,儿童也作为人的初始阶段得到了关注乃至迷恋。
卢梭被称为是西方第一个发现儿童的人,他写道:“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这个次序,就会造成早熟的果实…… 造就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卢梭认为儿童应当按照儿童自身的发展规律引导和呵护,发挥他们的求知欲、好奇心、热情和爱心,尊重他们的自由天性。更重要的是,他秉持自然主义观点,认为儿童比矫揉造作、事故老练的成人更贴近自然、高尚、更有价值,首次明确地将儿童的价值置于成人之上。当然,文化的变革往往是观念先行。在卢梭歌颂童年的时候,第一次工业革命正让无数儿童沦为生产线上的童工,受到比以往更加严苛的系统性剥削。中产阶级教育家的呼吁并不能抗衡资本主义对廉价劳动力的索求,直到二十世纪初,欧洲的儿童处境才逐渐改善,大部分能够接受基础教育。
中国现代童年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和社会改革、进步的迫切需求紧密结合。明末思想家李贽首倡 “童心说”,从童心可贵带出真心可贵,其目的是为了抗击成人社会虚伪不公的秩序、宣扬离经叛道的改革观念,可惜他的思想未能开花结果。从晚清到民国,“童年” 的观念和其他西方思想一道,作为舶来品进入中国,较早吸纳现代童年观的日本人在中国兴办的小学也从旁促进了中国现代儿童观念的形成。
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从洋务派到康梁,再到蔡元培、鲁迅一代新文化领袖,都特别重视儿童问题。对他们而言,儿童不仅是卢梭式启蒙观念中纯粹健全的人,重视儿童也不只是出于人道主义,更是因为在他们身上寄托了具体的期望。19-20 世纪,中国快速但波折的现代化进程是由迫切的民族独立诉求催动的。李泽厚曾说中国现代思想就是 “救亡压倒启蒙” 的过程。然而很多人随后指出,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启蒙本身就是为了救亡,树新人是为了建新国。在西方军事、经济、文化的多重压力下,改革者希望引进现代知识和思想以救国,又深感自己的见识根植于旧时代,吸收新知为时已晚。因此,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希望儿童在十几、二十几年后担当起匡扶国家的重任。
此外,正如卡林内斯库、哈贝马斯等人提出,也恰如很多读者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的 —— 现代社会是信奉线性进化、永恒进步的社会。人们每天都在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 未来一定会更好…… 这种信心渗入社会的每个毛细血管,影响人们各种微小的决定,也让人们自然盼望晚辈比起前辈,心智更聪慧、人格更健全,能带来更好的社会。总之,在中国现代化话语中,儿童不仅具有生理学上的意义,还带有鲜明的道德和政治意义:儿童是属于未来的进步力量;是民族乃至人类的希望。保护儿童,就是保护民族和人类的未来。
因此,教养儿童不是一项普通的社会分工,而是仁人志士共同的事业。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夏丏尊等名人共同制作小学课本;鲁迅、赵元任、严文井等翻译和创作儿童故事;冰心用儿童的口吻写诗,和小读者通信对话…… 成人世界的思想者踊跃地用幼稚的语言迎合儿童,是因为 “救救孩子” 是公认的紧迫工作。即便是相对保守的社会力量,在重视儿童的问题上也能达成一致。国民党热衷于组建童子军、举办儿童演讲、运动比赛,教育儿童 “我是中华国民,将来一定了不得”,并首次规定了每年 4 月 4 日是儿童节。共产党虽然对儿童宣传不同的思想,但同样过这个儿童节,教育儿童 “团结起来学做新中国的新主人”,对他们的总体期待并无不同。

和赞美童心一脉相承、共享一套逻辑的是崇拜青年。“青春崇拜” 是 20 世纪中国非常独特、有时代色彩的现象,已有很多中外学者讨论过。在通常的社会习惯中,年长的人看不起年轻人是常态。但在现代化思维和目标的驱使下,20 世纪初的思想者投向儿童的目光也同样投向了青年。青年在年龄、体力、现代知识方面的优势、他们对改革更开放的态度、更少的既得利益顾虑…… 都被政治化,让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从一个年龄阶段变成了一种进步的政治身份。陈独秀以《敬告青年》一文开启了新文化运动、鲁迅对青年人的求助几乎有求必应、乃至于钱玄同发表著名歪论 “人过了四十就该枪毙”,这些行为都是基于对青年这个政治身份的期望。
在重视青年的文化氛围之下,新文化运动乃至之后的大部分进步刊物,作者和读者都是青年;大部分社会运动,组织和参与者也都是青年。十几岁的学生组织大规模游行,在今天的年龄观念下可能是冒失、幼稚、添乱,但在革命年代却意味着青年愿意接过火炬,长远的未来大有希望。
共产党继承了新文化一代的欣赏儿童和崇拜青年。举一个很有象征意味的例子:大陆的小学课本长期使用一篇课文叫《飞机遇险的时候》,讲的是 1946 年周恩来等人乘坐的飞机遇险,救生伞包不够,周恩来将自己的伞包让给叶挺的女儿,11 岁的叶扬眉的故事。这篇课文之所以存在,当然是为了表现周恩来的高尚品格,但也侧面证明:遇到危险时,将生的机会让给儿童是毋庸置疑的高尚行为。在笔者的回忆中,教材没有提及,也不会引发这样的讨论:一国总理和普通的孩子一命换一命是否值得,是否应当?当然,扬眉将来可能成为更有价值的人,但在这个故事的语境中,她儿童身份天然的象征意义比她未来可能的实际价值更重要。这在今天恐怕绝非共识。
在现实中,20 世纪共产党对青少年的看重也令现在的人难以理解。只需举一个例子:李立三 27 岁、任弼时 23 岁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 24 岁大学刚毕业就成为了中央政治局书记(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总书记)。具体的任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形势,但也说明当时青年的地位和今天不同。这种青春崇拜很大程度上延续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只不过主要对象从知识分子式的五四青年变成了勤劳勇敢、敢于斗争的农村青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红小兵能立刻被动员起来心安理得地造成年人的反,和几十年来 “年轻人比长者更进步” 的观念培养出的主人翁意识有很大关系。甚至直到六四时,青年学生坚信推动改革是他们,而不是年长干部的历史使命,这种政治信念也是经由文革,继承自五四。
概括来说,20 世纪就是中国 “儿童的世纪”。人们将新的一代 —— 儿童和青年,作为一种社会资源而不仅仅是个人来爱护,背后是社会进步的观念和对未来的整体期待。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实践这种观念,但儿童和青年作为一种充满希望的符号(想想节日放飞和平鸽的儿童,“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少年强则中国强” 等标语)已经被社会广泛接纳。

2022 年 10 月 1 日,中国北京,孩子们穿著校服在天安门观看国庆升旗仪式。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儿童消失,只剩下投资品
把儿童视为成人应向社会缴纳的劳动力资源的催生策略,自然无助于人们用人文主义的柔情看待儿童,而只能换来 “我们就是最后一代” 的答复。
那么 21 世纪呢?环顾四周,情况已经起了变化。儿童作为文化符号越来越少出现,“祖国的花朵”、“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来的主人翁” 逐渐让位于 “熊孩子”、“四脚吞金兽” 这些贬称。青年则仅能在每年五月四日成为祖国的栋梁,其他时间都是社会的问题和病症。儿童和青年这两种政治身份相伴兴起又同时沉沦,既有六四依赖政权合法性和宣传策略变化的原因,也有时代整体观念变革的因素。
首先,绵延二百余年的恒久进步观念正在破产。中国文革后直到 21 世纪初出生的大部分人,从出生到成人目睹了 “小康社会” 的实现、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小到个人物质生活,大到国家经济水平和国际地位,总体都在进步和发展。然而最近十几年,即便是对政治领域的倒退毫不敏感的人也能感受到工资购买力的下降、学历的贬值、就业的缩水。
2023 年,中国更是出现了明显的通缩迹象🔗。百姓从 “消费升级” 变成 “消费降级”,对宏观经济的信心越来越差,通缩的情况就更难扭转。国际关系上,长久以来牵动中国人神经的 “与国际接轨” 叙事在 2008 年中国举办奥运会后达到巅峰,之后就因为中国国际关系恶化、树敌无数,乃至于和美国卷入新冷战而逐渐消失。通过被互联网长城隔绝的简中视角,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个有待闯荡、新鲜刺激的舞台,而是越来越危机四伏的黑暗丛林 —— 这或许也是就冷战和新冷战的区别之一:冷战至少部分是两种发展理念、社会理想之争,双方都奋力发展、上天入地,希望占据人类进步的先机;而新冷战则是一种单纯的零和博弈,没有路在何方,只有你死我活。
进步叙事失去了活力,作为其载体的儿童也就自然失去了光环。作家河森堡在微博上评论 “厌童” 的话颇中肯綮:社会上弥漫着有今无明、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气氛,不适合生养孩子这种超长线的投资。不过,把孩子视为投资,而不是有天然价值的宝贵之物,本身也是儿童概念失落的原因。因为说到投资,一定会涉及到:谁投资、谁受益?凭什么?
目前国家关于儿童的叙事非常直白粗暴:儿童就是今天播种、明天收割的储备劳动力(讽刺的是,青年作为今天的劳动力,则很难实现就业)。六四之后,革命叙事被从中共的执政合法性中剔除出去,宣传部门也小心翼翼,避免将在现代化逻辑中和革命相绑定的青年询唤为主体,再次掀起任何政治波澜。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之下,国家对青年的态度更是家长式的全权接管和刻意矮化,把一个时代的问题纷纷归结为一代人的问题。而对于儿童,私有化改革之后,儿童的社会养育被几乎全部转移给了家庭。儿童虽然还在公园玩耍、学校读书,但在公共的话语空间中已经彻底隐身了,既不是社会的责任,也不是社会的未来。二十世纪 90 年代时,中国用 “素质” 要求儿童,虽然修饰 “素质” 一词的也是人口和劳动力,但至少希望提升人力资源质量的国家和希望实现阶级跃升的父母之间有共同利益。
而现在,国家极力催生甚至逼生,已经不再讨论劳动力素质,而直接从最抽象的国家利益出发,给出劳动力供给、人口红利、老龄社会、退休金池等方面的理由 —— 既没有费神从意识形态层面进行儿童可爱、育儿高尚的宣传;也没有给父母提供有价值的帮助;更没有对这些儿童未来生活的世界进行任何规划。这种机械重复 “你给我生”,把儿童视为成人应向社会缴纳的劳动力资源的催生策略,自然无助于人们用人文主义的柔情看待儿童,而只能换来 “我们就是最后一代” 的答复。

而在私人领域,儿童也成为了一种非常个人的投资品,他不是祖国的希望,而只是一个家庭的前程。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总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儿童日益激烈的教育竞争不是为了其自身的健全发展,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社会资源。2023 年,经济学家陈文玲甚至公开表示:“子女也是消费品,是长周期的消费品,是可以带来给你长久回报的耐用消费品。所以,年轻人不生小孩是不对的。” 或许这位经济学家想说的是长期投资,但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如今的儿童都被放置在非常私人化的资本逻辑中,成为家庭的私有财产。在这种资本逻辑中,厌童就变得无比正常 —— 既然你的投资和消费无法给我带来收益,那么也不应该妨碍我。当然,总有人提出:现在的儿童是将来的社会保障支付者,人们应当放眼长远利益。但若真是 “在商言商”,谁会为了几十年后虚无缥缈的退休金,提前善待别人的孩子,甚至花重金养育自己的孩子?
言至于此,对比前文关于童年发现史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虽然现在儿童的存活率很高、生活条件也相对不错,但人们看待儿童的方式似乎在很多方面接近于现代儿童观诞生以前 —— 儿童是财产、商品、劳动力,而不是生命的一种形态、人的一个阶段,更不是某种集体希望的载体。在这波 “厌童” 讨论中,一些文章提到,这个社会已经容纳不下像一个儿童的儿童,而是用对成人(也让成人感到痛苦)的要求 —— 情绪平稳、安静克制来要求儿童。这和几个世纪前人们对小小年纪就工作谋生的儿童的态度不谋而合。只不过,中世纪的儿童尚有几年放任自流、胡闹戏耍的时间,而现代的儿童生下来就挤入了成人社会,成为父母的投资品、国家的潜在劳动力和他人的生存空间竞争者。失去对进步的期望的社会中,他们的未来一眼望得到头,道路却不管怎样追赶都拥挤而艰难。
当人们对这些孩子感到厌烦的时候,固然有合理或不合理的主客观具体理由,但也有共同的原因:人文主义、进步信念、民族诉求加诸于童年之上的滤镜已然破碎,如果人都没法被好好称作人,哪里又有儿童的位置呢?